【转】吴承学 | 学术研究入门的几个关键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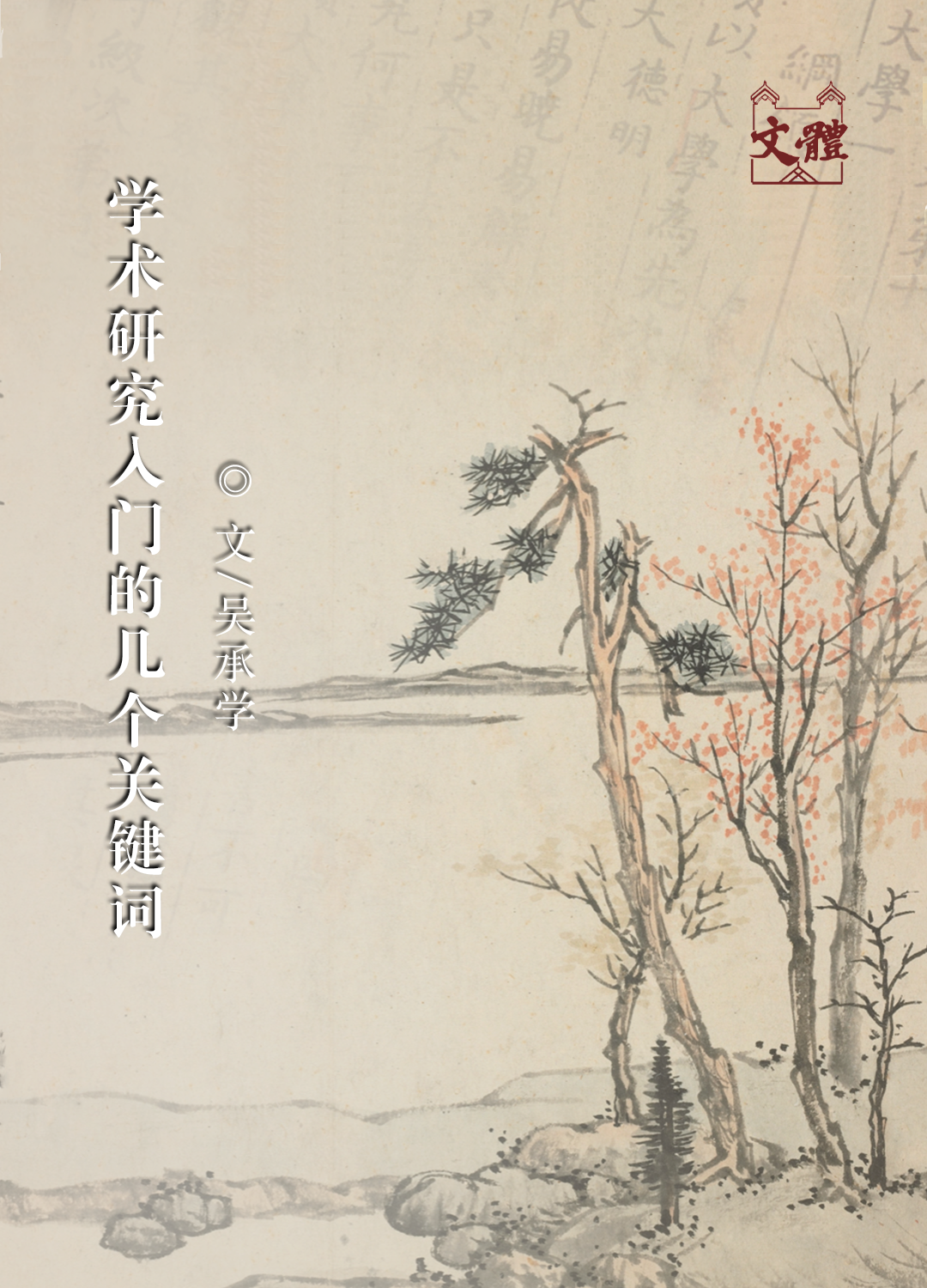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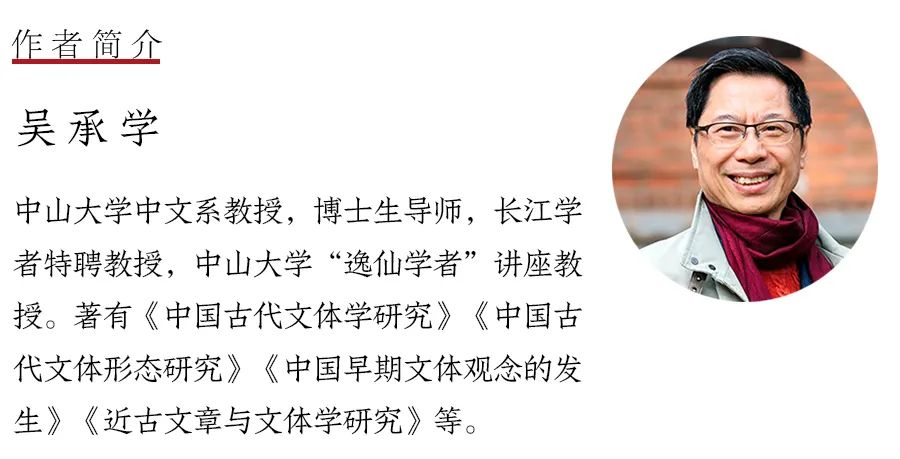
本文据吴承学教授2018年11月扬州大学
“长江学者谈读书与治学”讲座整理
今天为什么谈这个题目呢? 因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, 作为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,今年也是我们进入大学的第40 年。我们见证了改革开放,也亲历了 40 年学术研究的历程。40 年来,我看到了学术的发展轨迹,也目睹了不少学者的成长过程。我阅读了许多论著,成败参半;也浏览了不少论文,良莠不齐。我想对40年来的见闻和体会略作总结。总的来说,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关键词。

朱熹说过:“为学先须立志,志既立,则学问可次第着力,立志不定,终不济事。”王阳明给学生的学习指南,其中第一条也是“立志”。他说:“志不立,天下无可成之事。”对于读书人来说,要先立志,我们做学术研究,第一条也应当是立志。
人文学者要有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,做人文科学研究的人是文化的守望者和传承者。所以,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应当具有使命感,尤其需要有信念、信仰和信心,没有信仰就没有力量。我曾经作过一个比喻——治学如朝圣。治学应该像朝圣那样, 很虔诚、很敬畏。几年前,我为中山大学新生入学做过一场讲座,题目叫做《学术的尊严与快乐》, 后来发表在《博览群书》上。讲座中提到,我去过两次西藏,一次是 2006 年暑假,一次是 2013 年,途中经过青海。在西藏可以看到有的佛教徒,是从青海一直磕着长头,到拉萨去朝圣的。什么叫长头? 不是平常的磕头,长头就是五体投地,整个人趴在地上。据说,他们一辈子要磕十万个长头,从青海到拉萨,强壮的年轻人要走几个月,老年人则要走上一年。那里气候恶劣,在烈日暴晒下,磕着长头去朝圣。我们觉得很痛苦的事情,对于他们却是充满快乐的、很充实的。当我在西藏看到万里无云的天空,又看到虔诚的信徒,受到很大的触动。我觉得,那种有精神寄托的人,有执着信仰的人,心情是很沉静的。我讲的不是宗教问题,而是说做学术研究也要有一种执着的、虔诚的、敬畏的精神。

宋代的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说:“入门须正。”如果入门不正,越努力,离目标可能越远。经常有同学询问我:“怎么做学术研究?”我就想起欧阳修的故事。有人请教欧阳修怎么样写文章,有什么秘诀。欧阳修说:“无他术,唯勤读书而多为之,自工。”写文章没有什么诀窍,假如有诀窍的话,一个是勤读书,一个是多写,就这么简单。众所周知,欧阳修有一篇著名的文章——《卖油翁》。我们觉得很难的事情,不过手熟而已,每天坚持训练,必有所成。所以,做学术要获得一种学术感觉,获得了学术感觉之后就好办了。至于如何获得学术感觉,还是要靠自己去摸索。就像学游泳,即使有教练教,也一定要到水里慢慢体会,怎么浮起来,脚怎么蹬,手怎么划,要靠自己去获得一种感觉,在获得这种感觉之前,老师说多少都没有什么用。至于获得学术感觉的方法,其实也没什么秘诀,就是要多读、多写。
就我个人而言,写论文就像写字。学毛笔字,首先要临帖。要看古人怎么写,经历一个临摹的过程。以我的经验,可以选名家名作来学习。在通读论文之前,先看题目,再试想一下,如果由我来写, 我会怎样写、怎样立意,分析论文由哪些资料构成,该去哪里找资料, 如何谋篇布局等问题,然后再去看论文。经过预想,再和名家对比,就会发现差距在哪里。
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 如果一篇文章,没有经过斟酌就能想出来怎么写,那肯定是比较俗气的论文。与名家比对,找出差距,然后不妨先做模拟。我记得我刚开始学写论文,模拟最多的是钱钟书先生的文章。钱先生有一本书叫《旧文四篇》,收录了他以前写过的四篇论文。这本书虽然非常薄,但都是很经典的论文。后来钱钟书先生又增加几篇论文,出版了《也是集》《七缀集》。书出版过几次,我每次都会比较版本的差异。看名家的论文,就要把修改前后的版本放在一起比较,并思考他为什么修改,反复揣摩、临摹。

钱先生有一篇著名的文章——《“诗可以怨”》,我后来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上发过一篇《诗可以群》,就是模拟他的思路,虽然意思不大一样。我是讲魏晋南北朝的另外一种不受重视的文学倾向,谈文学的另外一个功能——“诗可以群”的。我的另一篇文章,发表在《文学评论》上,叫《江山之助》,是基于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里提到的一句话。刘勰认为,大自然会给作家带来灵感,让来自不同地方的作家作品染上地方的色彩,因而提出一个命题——“江山之助”。后来的学者很少去系统关注,所以我特意拈出这四个字,提出“中国古代地域风格学” 的话题。西方很多学者也谈到这个问题,我们的古人虽然很重视地域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,也谈了很多,但是研究者没有系统地收集研究。我做的工作是把它们系统地收集起来加以梳理,这也是模拟钱钟书先生的写法。写这篇论文的时候,我还在复旦大学读博士,写完博士论文,我就把这一章抄下来,寄给《文学评论》。那时候不认识编辑 ,但是很快就发表了。论文发表之后,编辑印象很深,所以我从那年开始,有一段时间差不多每年都在《文学评论》上发表论文,因为编辑觉得我的那些论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我觉得,这与临摹名家名篇是有些关系的。
有些人喜欢批评别人眼高手低,我倒觉得眼高手低是写作必经的过程,而且是好现象,至少不是坏事。为什么这么说? 因为在刚刚开始学术研究的时候,大多是眼低手低的,眼低手低的状态当然不如眼高手低。要先从眼手俱低开始,慢慢去辨识,最后得乎心、应乎手,才能达到眼手皆高的境界。所以,我劝大家一定要克服手生的问题。我们每天所接触的,大多是片段性的东西,思维也是片段性的, 如果突然有些想法,要及时地记录下来。
平时缺乏练习,是导致眼高手低的主要原因。我认识一位博士生,读过很多书,有很多好想法。但是他有一个缺点,就是平常不写。他的博士论文题目相当不错。可是没过几天,他却告诉我,写不下去了。过一段时间,他又给我看一个新题目,我说这个题目也不错,是可以做的。过一段时间, 又跟我讲,还是写不下去,又换了一个题目。这样大概有十次,换了差不多十个题目。结果到最后,还是写不成论文。这就是眼高手低,平常很多想法,却没办法把想法转变成有条理的文字,这需要平常多加练习。

我一直认为,对于学术研究,智慧比聪明更重要。聪明是天生的,但是智慧有后天的因素在。有恒心,又坚持,就会有规划。就像马拉松赛跑,要有恒心,一开始跑得很快,没什么用,很快会被超越。要有计划性,前面限速多少,后面的速度是多少,按照计划来。读研究生,各阶段要有比较严密的计划。做学问需要聪明,但不能太聪明。我见过有的人很聪明,天赋很高,反而未必是好事。因为他有很多种选择,比如说他能写文章,也可以去当官或者从商,都能取得成功,有无限的可能性,但歧路可能亡羊。而像我这样,就觉得除了读书写文章之外,别无所长。我就死了其他心,专门做学问,“一条道走到黑”。有些太聪明的人,可以选择的路很多,走来走去,走到最后,再回过头来想做学问,却已经迟了。有些人很聪明,喜欢赶时髦,流行什么就赶什么,没有长远的规划。我们应当找到自己最擅长的、有价值的东西,一直坚持下去。我自己在文体学方面的研究就坚持了差不多 40 年, 只要智商正常,慢慢挖下去,总能有所创获。如果自恃聪明,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,到最后,没有人会知道你。中国的学术浩瀚无涯,学者只要在某一领域被记得,就很了不起了。人们提到俞平伯,会想到“红学”;提到游国恩,会想到楚辞学;提到郭绍虞、朱东润、王运熙,会想到中国文学批评史……但提起许多学者,人们往往会茫然而问:他到底是研究什么的?
另一个方面的问题,是记忆力和创造力的关系。许多人认为学者应该博闻强记,确实,很多好学者的记忆力很强,但记忆力强不一定能做好学问。我认识一位老师,记忆力超强。他写过一本教材,上课时能一字不落背下来,但也没有任何新见。这给我一个启发,创造力比记忆力重要。有个电视节目叫做《最强大脑》,里面有些人记忆力特别好。但是你会发现,那些人里面,很少特别有创意的人。那些人大多从事创造性不是很强的技术工作。
再谈一个问题,做学问不能靠拼命,而要靠长命。真正的学术像马拉松,一定要持之以恒。有些人喜欢连续熬夜写论文,之后又连续睡觉,这样是不行的。尤其年轻人,一定要注意休息,不要把身体拖垮。身体不好,其他的意义就不大。

“悟入”这个词是借用宋人的说法,这里指对学术的领悟。举个例子,有很多学生在研究中会遇到找题目的困难。我认为,找题目的方法有两种。一种题目是在长期的阅读中遇到的, 或者说,是题目来找你,不是你去找它。另外一种题目是别人给的。我刚开始指导研究生的时候,就经常把我想要写的、有意义的题目给研究生写。后来觉得不行,因为对我合适的东西,对他来讲不一定合适。
每个人的学术背景、兴趣和学养是不一样的,最好的题目是应该在阅读的过程中遇到的,而不是被你追求到的,所以古人说“可遇不可求”,“遇”是无目的性的。苏东坡说陶渊明的两句诗,有两个版本, 一个是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一个是“悠然望南山”。他说,应该是“悠然见南山”,不是“望南山”。“望”是有意的,我想南山才会有意去望它。而在“采菊东篱下”的过程中,南山是在无意之中被看见的。所以他觉得应该是“悠然见南山”。这当然是审美的问题,而不是版本学的问题。学术研究也是一样,最好的题目是在阅读中发现的,而不是带着功利性去寻找的。反观当下,有的同学写论文,基本上都是去找题目。所以很多同学总是问我,怎么样去找题目? 我说,我从来就没有找题目,是题目来找我的。我是在长期读书的过程中,有所感触, 然后记录下来,以后就是一个题目。遇到题目和去求题目,两者差异是很大的。说得通俗一点,就像恋爱,双方最好是在相处之中自然而然产生感情,或者是在千万人之中一眼望去,瞬间产生特别喜欢的感觉。就像《九歌》所描写的:“满堂兮美人,忽独与余兮目成。” 遇到好题目,会有一种怦然心动、悠然心会的感觉。另外一种方式,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,不是自己遇到的,而是带着外在目的去求的,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所以,我强调的是,我们要在平常的读书里面去发现问题,而不是专门去求。
当然,凡事无绝对。自由恋爱也有以悲剧告终的, 也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,却一辈子很幸福。但是,相对来讲,自由恋爱的幸福感会多一点。当然这只是比喻。也有些同学做了老师给他的题目,最后做的很好的,不能一概而论。我只是说做学术的方法,应该是去遇,而不是去求。即使老师给了你一个不错的题目,今后的学术研究还是得靠自己在阅读之中去遇见。所以,无论如何,注重第一手资料、读原文原作、细读文本,都是最重要的。
我有很多选题是在对作品细读的过程中产生。举一个例子,传统有种说法:“诗能穷人,殆穷者而后工也。”这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个重要的命题。但是我有一次读宋代的类书,居然看到一句“诗能达人,达而后工”。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命题。这个命题不是我去找的,而是阅读中的感触,我觉得可以做文章。所以我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《“诗能穷人”与“诗能达人”》。在中国古代理论的原生态里面,两种命题都有,而且“诗能达人”,即诗歌能够给读书人带来好的命运,在当时更符合历史真实。唐代以后,以诗取士,诗歌可以改变读书人的命运,如果要走入上流社会,就一定要会写诗歌,社会的交际也需要写诗歌。宋代的理论家因此提出 “诗能达人”,而且是“达而后工”。你想一想,中国古代哪个诗人没有当过一官半职的? 按照现在的说法,中国古代的诗人大都是行政干部,哪个人完全是平民老百姓? 平民老百姓写的东西很少是第一流的。但如果只是把这个问题说出来,意义也不大。发现了这个现象,就要深入思考,它的意义是什么? 既然这样,我们中国古人为什么会在后来把“诗能达人,达而后工”逐渐淡忘与遮蔽,而是“诗能穷人,穷而后工”,“诗人薄命”,这些说法给我们的印象更深? 实际上,遮蔽与淡忘是一种选择,这种选择是中国传统诗学理想起的作用,不是诗人薄命,而是我们的传统诗学里面认为诗人应该薄命, 只有那些在生活中受到磨难的人,只有那些诉说人类苦难的作者,才是好诗人,只有那些描写人类苦难的诗歌,才是好的诗歌。这是一种认同与选择。不是诗人薄命,而是诗人被薄命。也就是说,这是中国古人的审美理想在选择,是价值的判断,是一种集体的认同。我们会觉得诗人不能养得白白胖胖的,是不是? 在我们的心目中,杜甫的样子就应该是那种穷愁潦倒的样子。屈原也是那样。杜甫长得就那么瘦吗? 其实不一定。很多东西其实是集体想象的结果,“诗能穷人”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。实际上,在中国古代,诗和诗人集体被赋予了一种悲剧的色彩。而虽然“诗能达人,达而后工”,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更真实,但是审美的意义不大。我从这个角度遇到这个题目之后,又深入去思考,这样的题目是遇到的。另外,不少同学在选题的过程中,经常走入一个误区,就是在老师讲课的内容里面去选题目,这是成功率最低的一种方法。因为老师讲的东西一般都是常识性的,在这个范围里面去找,很难找到好的题目,所以我还是提倡去自己发掘题目。

在学术研究中,眼光与悟性最重要。什么叫眼光? 眼光是一种带有专业性和个性的能力。比如一张X 光片或 CT 片,非专业人士看到的,可能就只是一张黑胶片。但是以专业眼光看,就可以看出身体哪些部位出了什么问题,这就是眼光。同样的文献,一个有眼光的人来看, 就能看出问题。换一个没眼光的人来看,就看不出问题。这也是指导研究生的时候,文科与理科老师的差异。理科的老师最重视的是仪器,有了仪器之后,让同学去实验,只要你严格按照规则, 所有人实验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。但是一段古文,老师读跟学生读结果是不一样的,不同的老师读的深度不一样,感受也不一样,这是我们人文科学的魅力所在,它在阐释上具有无比的丰富性。这可能与读者本身的背景、心态也有关。比如说一段文章,少年时读与老年时读相比,感受是不一样的。除此之外,读书的时候要注意上下文,如果不看上下文,读出来的结论可能完全是不一样的。
如果要发现问题,就一定要有悟性。比如读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,重复的“之”字有 20 个。我就再问同学们,还有没其他重复? 有的同学读了很多遍,还没有注意到。很多人说“读书百遍,其义自见”,假如没有带着问题,读书百遍,其义还是不现。其实《兰亭序》里反复出现了“怀”字,比如“游目骋怀”、“取诸怀抱”、“犹不能不以之兴怀”、“未尝不临文嗟悼,不能喻之于怀”、“虽世殊事异,所以兴怀,其致一也”等等,重复了 6 次。除了“怀”字,“俯仰”一词在《兰亭序》中重复了三次,比如“是日也,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。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”,这个“俯仰”是观察宇宙万物的姿态,所以“游目骋怀,足以极视听之娱,信可乐也”。而“夫人之相与,俯仰一世”,则是指人生短促,“及其所之既倦,情随事迁,感慨系之,向之所欣,俯仰之间,已为陈迹,犹不能不以之兴怀”。为什么用这么多“俯仰”? 在那个时代,“俯仰”一词用的特别多,比如嵇康的“目送归鸿,手挥五弦,俯仰自得,游心太玄”,陶渊明《读山海经》的“俯仰终宇宙,不乐复何如?”假如深入研究,你会发现,魏晋南北朝以来,“俯仰”这个词与玄学关系很密切,是从《易经》里面来的。那个时代的人很喜欢用“俯仰”来表现对天地的观察、对人生的态度、对宇宙的感慨。再把 “兴怀”与“俯仰”结合起来,可以做一篇文章,就叫做《“俯仰”与“兴怀”》,能够看出魏晋南北朝受到玄学影响的那些人的眼光和感慨。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,始终带着问题意识。

选题是很个性化的话题,每个人的选题应该都带有自己的特性,对于这个人是能做的,换一个人可能就不行。先谈谈选题的“忌”,题目不要太大或者太小。什么叫大,如果不能大致穷尽这个题目所需的文献,这个题目就比较大了。题目太大的话,太宏观,论文会写的比较空洞。题目太小的话,假如小题大做,能够有比较高的立意的话,是可以的,但是太琐碎就不行了。
第二个方面,是论题太熟的问题。很多人喜欢蹭热点,流行什么东西,他就跟着做什么,因为写出来的文章比较容易发表。但我恰恰认为,做学术不能蹭热点,人多的地方不要去,要有自己的个性、自己的坚持。假如你原来做这个东西,当然可以,但假如是去蹭热点,这样的学者是没有独立性的。如果一个学者,哪里有热闹,他就出现在那里,就可以判断不是好学者。学者毕竟不是演员。
题目也不能太浅。如果题目太浅,研究了半天,结果那东西不用研究,太浅俗。还有,题目忌太俗。题目好像一顶帽子,比如某个时代的什么东西,成为一个题目,过一段时间再套别的关键词。又比如说魏晋南北朝的什么东西,然后改为宋代的什么东西,又可以改为明代的什么东西,这样的题目都是俗的。最好的东西,是唯一的、有个性的、不能替换的。假如不是唯一的东西,一般来讲,就是俗。
最后一个,不能太险。太险是什么意思呢? 本来学术上存在争鸣是好的,但是有些题目,有争议性,就要注意。学位论文一定要稳妥,避免争议较大的选题。学术争鸣的文章,以后再做不迟。
另外,选题的时候也要慎重,不用拔的太高,要谨慎使用“原创”和“填补空白”这些词语。理工科的原创,是完全自主的纯粹的创造,从无到有的创造,我觉得是可以的。但是对于人文学科,原创性或者是完全填补空白的选题,其实是很少的。而且,原创的东西不代表一定有价值。比如你家里有一件传家的古画,其他人可能看不懂古画上面题的是什么字,你把它弄懂了,并且考证画上的章是什么样的,古画是怎么流传下来的,然后好好的保存下来,这是一种传承。算是原创吗? 不是,但是这种工作很有价值。反之,你家里本来没有垃圾,因为做菜产生了很多厨余垃圾,这些东西倒是你原创的。所以说,人文科学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开拓。
有些东西叫做“接着讲”,有些东西是“照着讲”,但是又有自己的东西,我觉得这就很好。我看到很多同学讲他自己填补了什么空白,我就觉得不太自在。我对同学讲,你不要整天填补空白,很多空白的东西不一定有意义。中国古代历史那么悠久,文献那么多,你要找一个没人研究过的东西,其实是很容易的。很多人提到填补空白,就引起我的警惕。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做学术研究,却没有人注意到,是特别难,还是说它没什么价值? 还是太琐碎,意义不大,所以大家才放弃了呢? 当然,假如你是发现了一种东西,是人家没有发现的,然后又很重要,那么我觉得这当然很好, 我不是反对填补空白,只是建议这种提法要很谨慎、节制。

做学术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立意。一篇论文的立意,古人称为“立主脑”,就像人的头脑,是最重要的部分,是论文的核心部分、中心论点,所有的论述都是围绕它的。一个人的文章写得清楚,是因为他的头脑清楚。一个人头脑清不清楚,直接反映在论文上。要注意几个问题。首先,“立意之先,务在清空”。苏东坡有诗云:“欲令诗语妙,无厌空且静。静故了群动,空故纳万境。”作文也如此。为什么要清空? 比如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,关于这个问题,我们会有很多“前理解”,也就是先入之见。这些先入之见可能是你从父母那里得来的,或者从书本得来的,或者从老师那里得来的,或者源自以前的一些不成熟的说法,在写论文的过程中,我们要把它先清空。然后,一切以文献来说话,不去相信任何人。材料能够说一分问题,就说一分问题,这样永远不会出错。前人的东西当然可以引用,但是要建立在这个材料是正确的基础上。所以,“立意之先,务在清空”,就是说不必执着于前人的观点或者自己的先入之见。
第二个问题,要有高度与深度,而不是就现象谈现象。举个例子,如果我们讨论一个女孩子,说她是不是处女,人家一下子会觉得很八卦,这个话题很无聊。而陈寅恪先生就写过一篇文章,讨论杨贵妃在进入皇宫之前是不是处女。这个话题的立意在哪里? 他把这个问题放在唐代民族融合的背景下,通过皇帝选妃并不在乎是不是处女,以小见大,考察唐代多民族文化风俗的融合,跟传统汉族的审美观、道德观、风俗是不一样的。在多民族融合的文化背景下,唐代的政治文化道德有些什么独特的地方? 他的立意在这里。再举一个例子,宋代的词人宋祁写过一句词叫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,清代的学者李渔说“闹”字不好,为什么不好? 因为争斗有声,“闹”字是诉诸听觉的。他说桃李争春就可以,没有听说用桃李闹春的,这是持一种批评态度的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里面则说:“着一‘闹’字,而境界全出。”他从意境角度谈词,说“闹”字写出了境界。两个人的理解完全不一样。王国维从境界来说,但是为什么会“境界全出”呢? 他没有从理论上去阐述。钱钟书先生《通感》立意的深度和高度就不一样了,他是从一种理论性、系统性的研究入手的。他举了古今中外很多类似的例子,然后概括出一种现象和规律。他提出一个观点,中国诗文有一种描写方法,古代批评家和修辞学家似乎都没有拈出。这种描写方法,借用西方的心理学的概念,可以叫作“通感”。通感就是在日常的经验乃至文学的描写里面,可以把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触觉打通。所以这个“闹”字本来是诉诸听觉的,但是好像视觉、听觉都打通了,更形象地把春天的热闹表现出来,不仅有色,而且有声。《通感》发现并总结了古今中外文学创作中的一种现象,他的立意比李渔、王国维都更高。
关于立意,还要注意一个问题,就是去俗避熟。我做《中山大学学报》主编时,每天看很多的论文,觉得多数论文的问题,一是在俗,一是在熟,没有新鲜感。所以写论文的立意要去俗避熟。你先设想一下,为什么要写,一般人会怎么样去写,会分哪几个部分去写, 然后你就要把一般人能想到的东西去掉,不要重复常识。就像剥竹笋,要把外面的硬壳一层一层地剥掉,只保留最鲜嫩可口的部分。但是很多同学写论文,不知道一定要去掉不用研究便能想到的东西,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这样做不是为了标新立异,是要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,说一般人说不出的话,是追求更深刻的东西。
最后一条,立意要精确到位,说到点子上。就像我们打鼓一样,打到不同的地方,声音是不一样的,打到鼓心的时候,声音最洪亮。所以立意要说到点子上。很多同学写论文,最后说不到点子上。说到点子上的好论文,其实不用长,关键是点到最核心的问题。

我们在写论文的过程中,要像打官司那样,给出很充分的证据,要有逻辑地形成证据链。在论证的时候, 心目中始终要有一个给你找茬挑刺的人,你说的每一句话,这个人都会提出疑问、反驳。你一定要很从容地、有证据地说服他。所以我有一个说法,叫“治学如治狱”,写论文就像自己与自己打官司一样。朱熹在谈读书法时说过:“看文字如捉贼,须于盗发处,自一文以上赃罪情节,都要勘出。莫只描摸箇大纲,纵使知道此人是贼,却不知他在何处做贼,亦不得。”(《朱子读书法》卷一)治学如治狱,犹如看书如捉贼,都需要细心体察,用充分的证据说话。

好论文是修改出来的。修改论文不在于次数多,而在于每次修改论文应该带有目的性。比如说这次解决标点符号的问题,下次专门解决结构上的问题。好的论文结构一定是密切关联的,善于写论文的人,每句话、每个段落之间都是有内在逻辑的。好的论文不能颠倒段落的顺序,假如你觉得你这篇论文可以颠倒顺序,那就是缺乏内在的逻辑性。另外,我喜欢请同行审读未出版书稿和论文,包括我的学生,希望他们给我多提一些意见。在接受意见时,也要有举一反三的悟性。比如我前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《晚明小品研究》,送给很多人看,请他们提意见。有时候,有人给我提一条意见,我就要把整本书的相关问题全部改正。比如有人提出一个问题,他说我很喜欢用“的”字,我后来一检索,果然,全文里面很多“的”字其实都是可有可无的,显得啰嗦。所以凡是可有可无的“的”字,通通去掉。然后,类似的“于”“了”等容易重复的虚字也适当删除,一下子少了很多字。

文献引用要穷源竟委,征实求是。以前,听一些老先生说,看一篇文章所引用的文献,就知道这篇文章有没有分量。此外,看看引用材料的版本也很重要。有些学者喜欢引用最容易找到的《四库全书》本,或是不专业的出版社,可能会出问题。比如《史记》,我建议引用中华书局的版本,这是经过许多专家研究、比较专业的版本,假如引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,版本很糟糕,行家一看就不行。另外,还要讲究“史源学”的问题,尤其是研究唐宋以后的很多文献,你以为这句话是这个人说的,其实他的意思可能是更早的人说的。我看到明代很多谈文体的论著,其说法其实是源自《文心雕龙》的,但没有注明出处。有些是完全照搬,有些是略有改动。古人是不讲知识产权的,但如果你引用他的话,以为是他的原创,就会让人觉得有些外行了。
原载柳宏、王定勇主编:《文本与视野——长江学者谈读书与治学》,凤凰出版社2021年。
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: 中国文体
目录 返回
首页
